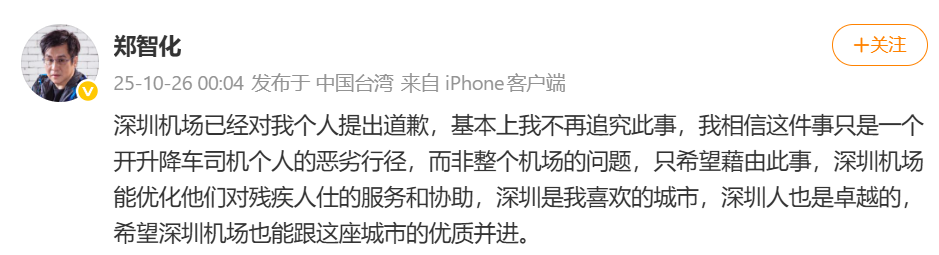清晨6点的南京江宁稻田,24岁的植保员林晓雨把裤脚卷到膝盖,踩着沾着露水的泥土蹲下来——她的眼睛几乎贴在稻叶上,指尖跟着一只稻飞虱的移动轨迹轻轻点:“第89头,第90头……”这样的动作,她和同事每天要重复近10个小时。
“不是闲得慌,是真的不能少。”林晓雨擦了擦额头的汗,手里的记录册上记着每块田的虫口密度:“比如稻飞虱,每百株稻苗超过50头就要预警,超过200头就得立即防治——差一个数,可能就是几十亩稻田的损失。”
这群“数虫人”里,有刚毕业的植保专业学生,有做了5年的老员工,最拼的一次,他们从早8点蹲到晚7点,数完12块田,总共31200头虫子。“蹲得腿麻了就换个姿势跪会儿,手指被稻叶划得全是小口子,涂了风油精继续数。”23岁的实习生陈阳说,一开始觉得“数虫子”是“体力活”,直到跟着师傅去给农户指导防治,才懂其中分量:“去年夏天,我们根据数虫数据提醒周庄的王大叔提前3天打药,他的10亩稻田没受稻飞虱影响,比隔壁田多收2000斤稻子——那时候才明白,我们数的不是虫子,是农户的‘粮袋子’。”
在无人机、智能传感器普及的“数虫子”这份“笨活”反而成了农业里的“刚需”。“智能设备能测大范围虫情,但每块田的小环境不一样——田边虫子多、中间少,树荫下繁殖快,只有人工数才能精准到‘每百株’的密度。”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张工程师解释,“就像医生把脉,机器能查指标,真正的‘诊断’还得靠‘手摸’‘眼瞅’的细功夫。”
一开始不理解的农户,现在成了“数虫人”的“线人”。“我以前觉得这群娃蹲田里‘瞎捣鼓’,直到去年他们帮我躲过螟虫灾。”58岁的农户刘建国说,现在只要看到田里有虫子,他都会拍照片发给林晓雨:“这群年轻人的‘笨活’,比我种30年田还管用。”
夕阳西下,林晓雨抱着记录册往工作站走,册子里的数字歪歪扭扭,却写满认真——每一个数字背后,都是对土地的敬畏,对“把事做细”的坚持。“有人说我们‘过时’,但我觉得,现代农业不是淘汰‘笨活’,而是把‘笨活’做到极致。”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工作证,上面“南京市植保员”几个字,在夕阳下泛着暖光。
风里飘来稻叶的清香,远处的稻田里,又有几个年轻人蹲了下来——他们的身影,和稻田融成一幅画,画里写着:所谓“新农人”,从来不是“高大上”的代名词,而是愿意沉下心,把“数虫子”这样的小事,做成保护粮食的大事。